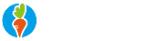早期采用数字技术和在纽约市建筑“压力锅”工作的竞争性质帮助SHoP建筑师事务所取得成功,校长格雷格·帕斯夸雷利和约翰·塞罗内在这次采访中说。

Pasquarelli是1996年创立SHoP建筑师事务所的五位建筑师之一,而Cerone自2008年以来一直是员工,自2020年以来一直担任校长,他向Dezeen讲述了该工作室的起源,该工作室最近的项目包括布鲁克林大厦和111 W 57th,这是世界上最瘦的超高层摩天大楼。
布鲁克林大厦(Brooklyn Tower)最近达到325米的顶峰,现在是布鲁克林最知名的地标之一,部分原因是特殊的分区,这意味着它几乎可以从自治市镇的任何地方看到。
“这座建筑 - 这是唯一一座针对这种高度划分的建筑 - 我们知道会有点像布鲁克林的帝国大厦,”帕斯夸雷利说。
“我们想确保无论你在什么网格上,无论你在布鲁克林的哪个地方看它,你都觉得你在看前面。
他补充说,建筑师应该“在布鲁克林建造严肃的建筑”,而不仅仅是在曼哈顿。
“布鲁克林五大建筑中的两座”
“为什么布鲁克林应该有一座二年级的塔楼?它有一个真正的天际线。这是一个很棒的居住地,“他说。“我为我们做了那座建筑感到自豪,我为我们做了巴克莱中心感到自豪,”他说,指的是工作室在2012年开放的19,000个座位的体育场馆。
“也许有了布鲁克林博物馆,奇迹轮和布鲁克林大桥,我们得到了布鲁克林五大建筑中的两座,我感到非常自豪。
校长们将他们在纽约市取得的成功与SHoP在建筑过程中早期实施数字技术,与开发商密切合作的意愿以及该市的竞争性质联系起来,Pasquarelli称之为建筑“压力锅”。
“纽约和这里的人们的强度确实影响了这个项目,”帕斯夸雷利说。
“纽约总是在变化。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但它需要是真实的,人们可以分辨出某些东西是被迫的,而不是真实的,“Cerone补充道。
波特豪斯 SHOP 建筑师事务所
肉类包装区的波特之家有一个完全基于数字文件制造的立面。照片由郑权执导
SHoP很早就采用了一些技术,使他们能够以数字方式规划华丽外墙的制造,例如在巴克莱中心和波特之家(Porter House),这是一座具有定制制造立面的建筑,与曼哈顿肉类包装区的一座旧建筑悬臂。
创建非常详细的制造计划,有时甚至帮助支付实验方法的成本,有助于向开发人员证明这种方法。
“我们当时想,看,这是纽约,”帕斯夸雷利在公司成立之初期时说。“我们都在为这个岛屿的每一寸土地而战。如果我们不参与并使用开发人员的语言进行交谈,我们将永远无法真正构建和推动我们所能做的极限。
玛丽娜·塔巴苏姆·索恩建筑奖章
Pasquarelli说,这项技术使工作室能够通过提出原理图模型来实现设计期望,这些模型不仅显示了建筑物的外观,还显示了如何建造它们。
“我希望记者们能够对过去20年进行渲染与现实的批评,并像我所有的竞争对手一起回顾,展示他们的渲染效果如何以及最后建筑的样子,”他说。
“并评价建筑师如何兑现他们的承诺,因为我知道我们将赢得竞争。
为了美丽的建筑而技术
对于专门从事生产技术的Cerone来说,该技术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也是避免“噱头”的一种方式。
“所有技术都不是为了技术本身,而是为了使这些美丽的建筑变得重要,”Cerone说,并补充说工作室正在完善一个系统,该系统将允许数字数据库为承包商和开发商提供SHoP设计各个方面的规格和制造元素库。
虽然该团队强调了简化生产并与开发人员沟通以提高效率的重要性,但他们也承认一些项目所代表的财富差距。
111 W第57街
曼哈顿西57街111号是世界上最瘦的超高层摩天大楼。照片由大卫·桑德伯格/埃斯托提供
“我是纽约人,我关心这座城市,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亿万富翁街,”帕斯夸雷利说。“我明白贫富差距的论点,但是,如果他们要上升 - 而且他们会上升 - 让它成为最好的。
“无论是布鲁克林大厦还是西57街111号,我们都与客户一起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即尽管非常富有的人将住在这栋大楼内,但我们每天有八百万人必须与它一起生活,”他继续说道。“所以你需要在外面花的钱至少和你在里面花的钱一样多。
他们说,流程和技术驱使他们创造适应这个地方的建筑。
“人们在巴克莱自拍,然后转身,然后在布鲁克林大厦的街道上自拍,”塞罗内说。“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同一个建筑师。
高耸的布鲁克林大厦,毗邻较短的摩天大楼
人们与布鲁克林大厦(中心)自拍,SHoP说。照片由SHoP建筑设计事务所提供
虽然纽约不再是公司的主要关注点,但负责人认为,他们的方法和风格,在形式和功能上各不相同,已经在这座城市留下了印记,并允许他们向国际客户证明自己。
该工作室的全球建筑包括米兰和曼谷的大使馆,博茨瓦纳庞大的政府大楼以及从布鲁克林塔汲取灵感的荷兰摩天大楼。
“因此,在最初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专注于纽约。一旦我们证明我们可以建造它们,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说,你能在其他地方做吗- 你能在非洲做吗,亚洲能做到吗?“ 帕斯夸雷利说。
“现在才刚刚走出去。
请继续阅读编辑后的采访:
Ben Dreith:作为学生开始在纽约进行设计,并最终负责该市一些最受关注的建筑,这意味着什么?
格雷格·帕斯夸雷利:我认为我们是在一个非常奇怪的时刻开始的。1990年代出现了大萧条。我是使用数字设计开始的一部分,就像使用动画软件一样。我们使用的是一些最早的3D打印机。我们处于数字化的最初阶段,看到了它将如何改变事物。我们工作的一些人正在使用它,比如弗兰克·盖里和格雷格·林恩,但他们用它来画画。
我们很早就想在纽约工作。我们都去了哥伦比亚。我们想从这里开始,我们想在纽约的压力锅里学习,不仅知道如何建造激进的建筑,而且建造具有经济意义的建筑,以及你无法建造的建筑。
因此,这些疯狂的形状即将到来,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将这些信息提取成美丽的东西?我们很早就开始接触激光切割机和3D打印机,我们早期的一些工作是将数字提取到可见光中进行实验。
此外,总有一个想法认为与开发人员合作是不好的,要注意它。我们当时想,看,这是纽约。我们都在为这个岛屿的每一寸土地而战。如果我们不参与并使用开发人员的语言进行交谈,我们将永远无法真正构建和推动我们所能做的极限。因此,我们没有责怪他们很困难,而是说他们的语言并激励他们做得更好,这在公司成立之初就非常多。
本·德瑞斯:现在做数字渲染是如此流行,你知道,这几乎是主流。当你第一次带着这些想法来找开发人员时,你有什么反应?
格雷格·帕斯夸雷利:他们认为我们完全疯了。维珍航空聘请我们担任肯尼迪机场的头等舱休息室,我们以数字方式制作了屏幕。我们和港务局的人打交道,他们有点像'你不能建造这个',我们说'是的,你不能,但机器人可以。他们说'你不要告诉我如何建造。然后就像五八年后,你和同样的人在一起,他们说,'哦,我们会找一个五轴铣床机器人来雕刻它。
从1998年到2006年,全世界对使用这项技术的理解都发生了变化。我们相信这一点,但这是我们能够与那些年纪大得多、拥有更多资源的公司竞争的一种方式。“他们太老了,无法理解计算机。因此,让我们利用这一点,尝试并能够建造这些建筑物,“我们说。
因此,使用这些数字工具从PS1开始。它始于我们长岛东端的公园。我们在那里做了一个实验建筑,一个摄像机暗箱, 这是第一座建筑, 建筑的每个部分都是在这个小展馆里用数字方式制造的。然后是波特之家,这是我们在肉类包装区做的第一座开发建筑,也是第一次对整个立面进行数字化制造,然后这项技术直接导致了能够拉动巴克莱中心。
我们被安排在纽约的那个高压锅里,必须高度理论化,设计非常激进,但超级称职,直截了当,经济负责。
本·德瑞斯:约翰,你大约从巴克莱时代开始。技术方法是否吸引您加入公司?
约翰·塞罗内:公司的精神是吸引我的原因。设计建模在本科时相对较新。但是人们开始进入[3D]建模来制作渲染图。我意识到你可以使用建模来指导。没有其他地方真正使用这些工具进行生产。这本身就与众不同了。因此,我被邀请从事生产技术,不仅将其用于渲染器 -我们有渲染器 - 而且作为与制作建筑物的人进行交流的一种方式,因此使用我们的设计模型,使用工具创建有关如何制作作品的说明。
格雷格·帕斯夸雷利:我们很早就知道,这种平面剖面和立面的想法是一种糟糕的沟通方式。因此,你有一些建筑师,他们在三维空间中思考得非常好,然后我们将这些信息简化为2D部分,将其交给其他了解您要做什么的人,然后他们必须提取这些信息。我们当时想,我们为什么要推动它完成这个过程?当我们能够利用拥有所有其他信息的数字并发明新的通信方式时。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些建筑就不可能建成。在纽约的压力锅里做这件事是我们必须经历的证据。因此,我们在头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专注于纽约。一旦我们证明我们可以建造它们。然后我们刚刚开始说,好吧,你能在非洲的其他地方做吗,亚洲能做到吗?就像它现在刚刚走出去一样。
本·德瑞斯:您的建筑类型涵盖许多不同的用途。这来自纽约吗?从为城市建造而不是建立类型学?
格雷格·帕斯夸雷利:在纽约,每条街道都是不同的。每个角落都是不同的。每个社区都是不同的。你走在那条街上,就有那种能量。这就是使它成为一个有趣的地方的原因。因此,也许我们用类似的方式来思考建筑,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我们只是在做塔楼,或者我们只是在做图书馆,或者我们只是在做公园,或者我们只是在做NBA竞技场,或者机场,它总是看到同样的事情,为什么这样做?有趣的是,每次拿出一个新的方法,我该如何解决问题?不是我该如何重复这项技术?我认为这恰恰来自于作为纽约人。我们喜欢这一点。
本·德瑞斯:再加上技术创新,为什么保持历史方面很重要,例如维护布鲁克林大厦的或使用兵马俑111 W 57?
格雷格·帕斯夸雷利:我确实在这里长大,那里有这样的背景,有一种存在的结构。修复建筑物是一种痛苦,对吧?我也认为这是DNA的一部分,有助于推动建筑的设计,对吧?但是,我们能从这里的东西中提取什么,它的背景,它的历史,叙事,故事,所有那些驱使我们创造新的和新鲜的东西,同时回顾和前进?所以我喜欢在现场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建筑, 因为它给了你一种可以借鉴的质感。我发现这非常有趣。我喜欢看到这些塔楼,感觉就像是历史建筑的一部分,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矛盾在纽约。
本·德瑞斯:技术方法如何仍然为人为因素留有余地?
格雷格·帕斯夸雷利:我们的一座建筑完工了,就像你看着它,你会想,哇,这感觉就像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我总是看到人们在我们的建筑物周围,他们微笑,他们指着我,或者他们对我大喊大叫。对于我们来说,建筑物不会在建筑物撞到人行道时结束。右?就像,这也可能是纽约的事情。这就像,有这些社区,事情正在发生,公园里有基础设施和地铁,开放空间和光线以不同的方式照射。建筑物下降到这种能量中,它向外辐射能量。我喜欢把建筑看作是这两种能量之间的中介。
约翰·塞罗内:因此,所有的技术都不是为了技术本身,而是为了使这些美丽的建筑变得重要。
格雷格·帕斯夸雷利:纽约和这里的人们的强度确实影响了这个项目。
约翰·塞罗内:纽约总是在变化。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但它需要是真实的,人们可以分辨出某些东西是被迫的,而不是真实的。
本·德瑞斯:巴克莱中心就是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它被公众看到和使用。你如何看待它与布鲁克林大厦(Brooklyn Tower)等建筑之间的对比,每个人都能看到,但也有一个更加封闭的方面?
格雷格·帕斯夸雷利:一个是私人的,一个是公共论坛,所以它们会有所不同。无论是在布鲁克林大厦还是在西57街111号,我们都与客户达成了这样的立场,即尽管非常富有的人将住在这座建筑内,但我们中的八百万人每天都必须与它一起生活。所以你需要在外面花的钱至少和你在里面花的钱一样多。我们需要考虑细节和材料性,以及从各个角度看待建筑物的方式,就像我们考虑公寓的布局一样。我认为,拯救这两座地标性建筑,让它们可以公开进入并融入到建筑中,而不是把它们推倒,建造一个在外面有门卫和安全的堡垒,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互动。
所以在40英尺处有互动 从一个街区远的地方进行互动。这是10个街区外的互动。在拉瓜迪亚(LaGuardia)中飞行的互动,看到天际线上的建筑物,并认为所有这些级别都非常重要。在111上,因为它在曼哈顿,而且它是一个网格,你总是知道建筑物的主要和次要方式将被观看。这就是为什么兵马俑在两边,玻璃在另一边。在布鲁克林,所有的网格都是不同的,对吧?它们都相撞了。而这座建筑,是唯一一座被划为这种高度的建筑,我们知道它有点像布鲁克林的帝国大厦。我们想确保无论你在布鲁克林的哪个网格上,无论你在布鲁克林的哪个地方看它,你都觉得你在看前面。因此,建筑物的互锁六边形赋予了它一种能力,你从来没有感觉到你在看侧面或后面,而另一件事是你总是在看斜面上的两个立面。因此,通过将纹理放在建筑物上,它使建筑物看起来很坚固,而不是全部是玻璃,我们觉得这很重要。看到那座坚固的建筑给你的天际线上的那种引力,它变成了这个锚点,它变成了一个定向装置,这是我们思考当它从中心辐射出来时需要做什么的很大一部分。
本·德瑞斯:特别是当它与曼哈顿的塔楼竞争时。
格雷格·帕斯夸雷利:为什么布鲁克林应该有一座二级塔楼?它有一个真正的天际线。这是一个很棒的居住地。不,在这里做严肃的建筑。我为我们做了那座建筑感到自豪,我为我们做了巴克莱中心感到自豪。也许有了布鲁克林博物馆,奇迹摩天轮和布鲁克林大桥,我们得到了布鲁克林前五大建筑中的两座,我感到非常自豪。
本·德瑞斯:对于您和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来说,在这些建筑物上工作的感觉如何?
格雷格·帕斯夸雷利:这真是太神奇了。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团队来自世界各地。当原来的世界贸易中心正在上升时,我住在皇后区,我可以从卧室的窗户看到建筑。我保留了贸易中心的乐高模型,就像我小时候一样看着塔楼。令人惊讶的是,我为我工作的这些建築物感到难以置信的骄傲,因为我是纽约人,我关心这座城市,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亿万富翁街。我明白贫富差距的论点,但是,如果他们要上升,而且他们会上升,那就让它成为最好的一个。
约翰·塞罗内:
我就住在那儿。人们在巴克莱自拍,然后转身,然后在布鲁克林大厦的街道上自拍。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同一个建筑师。但这些是推动他们兴趣的东西,这就是有效和适合设计的东西。这是过程。人们认为用技术制造的东西需要以某种方式看起来。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们可以适合面料,并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风格。没有人会认为兵马俑,这种历史材料,会是数字制造的,所以它不应该是“技术人员”的样子吗?不,它看起来非常优雅。这当然是非常感性的。这是非常有音乐性的。感觉就像一架钢琴。感觉就像一座摩天大楼。它感觉像诱惑,感觉像材料,感觉旧,感觉新。就像那时候,当你觉得好吧,这项技术把我们带到了那里。
本·德瑞斯:现在技术已经赶上了该领域的其他领域,你还有来自开发人员的同样的阻力吗?
格雷格·帕斯夸雷利:以前,我们必须像一个彻头彻尾的啦啦队长,像拉拉技术一样。现在他们说,好吧,我看到它是如何工作的,哇,这很聪明。我们也想要这样。所以,它更容易拥有。但我认为这仍然是关于这座建筑的叙述。叙事让每个人都感到兴奋,然后正是技术使我们能够构建它并使其工作并获得这种高质量的构建。
约翰·塞罗内:在这一点上,他们相信我们。他们相信你向他们展示的图像会看起来像这样。它会的。
格雷格·帕斯夸雷利:在设计界,建筑的整个方面就像是,'你为什么要给客户做决定的权力?事实恰恰相反。开发人员也是如此。一旦我们和他们在一起,他们觉得他们在游戏中有皮肤,就像我们在沟通一样,他们让我们随时设计。
我希望记者们能对过去20年做一个渲染与现实的批评,就像回到我所有的竞争对手面前,展示他们的渲染是什么样的,以及最后建筑的样子。并评价建筑师如何兑现他们的承诺,因为我知道我们将赢得竞争。
本·德瑞斯:是否有任何技术让你感到兴奋,它们对任何即将到来的项目来说都是新颖的,或者你刚刚开始使用?
约翰·塞罗内:可视化工具。我们想首先解决非常困难的问题,比如如何使用计算机制造数百万个零件——这可以说是建筑的一个困难部分。我们先去那里,然后我们意识到这个行业并不是为了自动化生产管道而建立的。我们仍然上传图纸和所有这一切。因此,我们一直在幕后进行,使技术更容易通过应用程序获得。现在,如果你登录,这是预算的样子,这是你的项目的状态,我们称之为一种鸡尾酒时光应用程序。以下是对项目的直观实时访问。我们是否需要创建平面剖面和立面以及所有这些传统的东西?不,这是一个项目,这是它正在建设的地方。如果您愿意,可以实时获取更多信息。这是透明的沟通。没有人会打开这些3D建模工具;他们不应该这样做。客户和合作者不需要知道厚模型。这很有趣,因为通过直观的技术创造更多的项目访问和透明度,使我们能够做更强大,更深入的面向客户的技术。
格雷格·帕斯夸雷利:谁会进入这三百页的图纸?他们只想看到它。比如“我在哪里?我的公园在哪里?我的门面在哪里?有多少人在那里?同样的信息流向了幕墙制造商,同样的信息也流向了制造进入立面的玻璃的人,同样的信息也流向了制造将玻璃固定在立面上的螺栓的人。它使它对每个人都是透明的。
约翰·塞罗内:我们允许人们在他们的建筑存在前两年走过他们。在流程的早期,您会看到类似于时间线末尾的渲染。我们可以在第一个月就从概念上做到这一点。他们在他们的空间里,他们可以开始以更有趣的方式做出决定。
这不是噱头。你创建任何技术解决方案的唯一原因就是用一个小团队快速解决一些直接的问题。所以在本文的最后,你有一个路线图。这是以数字方式进行项目的方式。我们在基于云的系统中,我们可以从纽约的设计中完成所有这些工作,你知道,项目协调到螺栓,然后把这些东西发出去。
标签:
版权声明:本文由用户上传,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